



本文部分图片可能会引起不适
但是,这就是真实的世界
东非
乌云如巨幕一般
遮盖了一半的天空
在闪电和暴雨之下
青草正在茂盛地生长
而在太阳照耀的另一半天空之下
已经干燥枯萎的草原发出金色的光芒
(请横屏观看,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的草原,摄影师@李佳)
▼

在金色的草原上
3000多只狮子
1000多只花豹
200多只猎豹
以及数百只鳄鱼等捕食者
正凝神屏息,蓄势待发
(狮子,图片来源@VCG)
▼

秃鹫、秃鹳、鬣狗等食腐动物
正在远处按兵不动
时刻等待着机会
(秃鹫,图片来源@VCG)
▼

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的
是一场蓄意已久的谋杀
“凶手”似乎已经近在眼前
然而事实的真相
远比看上去要复杂
循着一点点线索
我们从一只迁徙的队伍
追溯到宇宙星辰
01
迁徙
这场“谋杀”的可能受害者
是一支由150余万只角马
30余万只斑马
20余万只瞪羚
以及不计其数的其它食草动物
组成的长队
(请横屏观看,迁徙中的斑马和角马,图片来源@VCG)
▼

它们的生活范围
主要位于非洲大陆东部
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境内的草原
这里被划分为几个国家公园
以及保护区、禁猎区和狩猎管控区
(东非动物大迁徙涉及的几个主要的国家公园、保护区、禁猎区和狩猎管控区在非洲的位置,制图@巩向杰&张靖/星球研究所)
▼

数百万计的食草动物
每年都将从塞伦盖蒂草原东南部
一路向西,向北
走过草原,趟过河流
到达北边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
再从东部向南折返
来回的路程超过3200公里
相当于从拉萨到沈阳的距离
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就是
东非动物大迁徙
(东非动物大迁徙的路线,制图@巩向杰&张靖/星球研究所)
▼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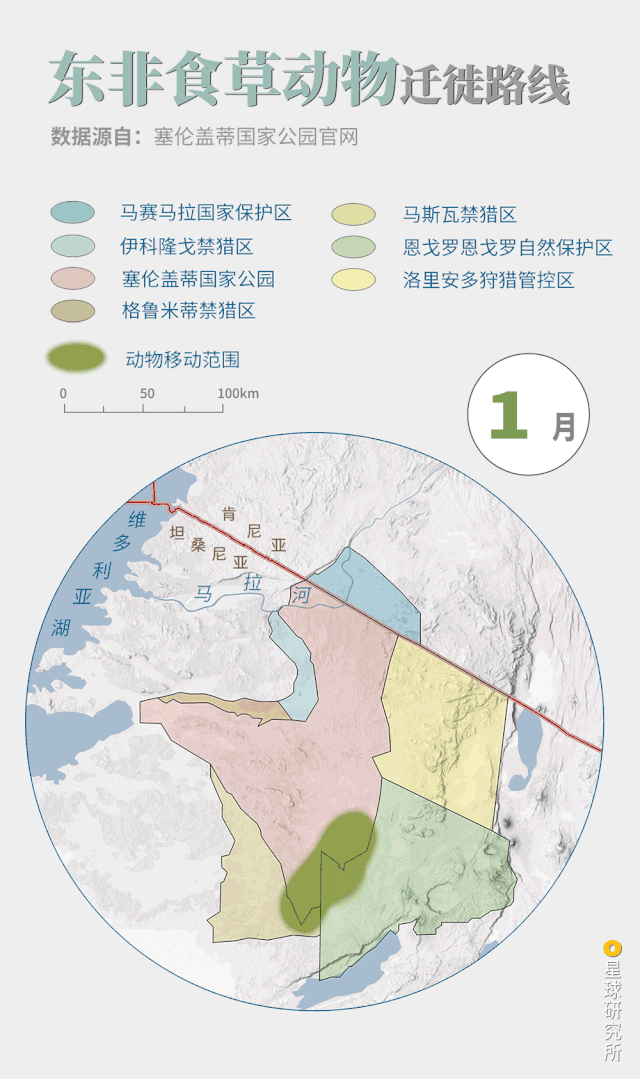
走在前面的是斑马
它们坚硬的牙齿
和高效的消化系统
让它们得以对付
纤维粗糙的草茎
(斑马,摄影师@胡子捷森)
▼

角马的肠胃更加娇嫩
斑马啃食过后留下的柔嫩草茎
成为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
(角马,摄影师@陈小琳)
▼

以数量取胜的角马
迁徙队伍的规模是斑马的5倍
它们走到哪就把那里的青草一扫而空
再边走边反刍细细咀嚼
这大大提高了采食效率
使得角马能迅速扫荡一片草原
(请横屏观看,塞伦盖蒂角马群,摄影师@蓦然白里小三黑)
▼

角马和斑马组成的大军
每天消耗6000多吨青草
同时产生3800多吨粪便
刚被啃食一空的草原在肥料滋养下
再次长出星星点点的嫩芽
但它们并没有得到复辟的机会
因为紧随其后
一队种类丰富的羚羊大军
正奔腾跳跃而来
瞪羚、长颈羚、大羚羊...
它们如一台台高效的活体割草机
扫荡过刚刚泛青的草地
(塞伦盖蒂草原上的瞪羚,摄影师@陈小琳)
▼

食草动物之间
构成了一个完美的采食序列
它们相互依存又避免竞争
物尽其用又不会赶尽杀绝
以至于每平方千米的草原
足以养活4、5万只大型食草动物
(请横屏观看,斑马、角马和瞪羚采食不同种类的草或草的不同部位,制图@张靖/星球研究所)
▼

不断迁徙的食草动物大军
激活了草原上的食肉动物
食草动物的数量
虽然是食肉动物的数百至数千倍
但食肉动物大多在固定的领地活动
无法跟随食草动物而迁徙
而猎物也不会束手就擒
因此为了获取食物
捕食者们必须身怀绝技
它们或是以强大的力量
在对峙中占据上风
(公狮捕食,图片来源@VCG)
▼

或是凭借团队合作
提高猎杀的成功率
(两只母狮合作追击水牛,图片来源@VCG)
▼

当然它们也并非总是最终的赢家
面对强大暴躁的对手
有时也不得不落荒而逃
(一只母狮被水牛攻击而逃跑,图片来源@VCG)
▼

食草动物强健的蹄、锋利的角
时常让捕食者吃尽苦头
(在捕猎中受伤的狮子,摄影师@程晓敏)
▼

即便成功获取猎物
也要尽快藏到隐秘的树上
以防被其他捕食者攫取劳动果实
(在树上享用食物的花豹,摄影师@李佳)
▼

而这场追与逃的大戏
随着迁徙大军横渡马拉河而进入高潮
马拉河全长近400千米
流域面积达到10000平方千米
是塞伦盖蒂最大的河流
连续的降雨让河水暴涨
陡峭的河岸更增加了渡河的难度
(马拉河及两岸,图片来源@VCG)
▼

更重要的是
河里生活着非洲最大的鳄鱼
尼罗鳄
它们体重可达200公斤
嘴中的60余颗利齿不断再生
仿佛一台活体绞肉机
静待着第一位落水的访客
(一只尼罗鳄吞下了一只瞪羚,图片来源@VCG)
▼

马拉河南岸的青草很快被消耗殆尽
狮子、花豹、猎豹等捕食者紧追不舍
河的对岸青青长草随风摇曳
前有食物,后有追兵
食草动物的选择只有一个
渡河
在经过多次试探和反复后
第一位勇敢者
终于决绝地跃入奔腾的河水
(一只角马跃入水中,图片来源@VCG)
▼

但实际上
潜伏水中的鳄鱼并不急于进攻
它们在选择合适的目标
领头者通常能够安全地渡河
先行者成功的经验
似乎产生了不小的激励
更多的角马开始接连下水
(角马群渡河,图片来源@VCG)
▼

随着渡河者数量的增多
仿佛闸门终于被打开
生命的洪流与冰冷的河水
在顷刻间交汇
(大队角马渡河,图片来源@VCG)
▼

而场面也逐渐趋向混乱
它们争先恐后,慌不择路
以至于在陡峭的河岸上
自行跳下的和被推挤下来的角马不计其数
它们在渡河之前就直接摔死在岸边
(从陡峭的河岸上向下跳的角马,图片来源@VCG)
▼

静待时机的鳄鱼也露出本性
之前看似平静的河水成了死亡陷阱
(鳄鱼咬住了一只斑马,图片来源@VCG)
▼

这场宏大而混乱的渡河“战役”
被称为马拉河之渡
堪称天河之渡
几个小时后
混乱逐渐平息
只留下尸横遍野
尸体甚至顺流而下堵塞了河道
(马拉河之渡中死亡的角马的尸体,图片来源@VCG)
▼

拥有食腐习性的生物闻讯赶来
其中斑鬣狗的咬合力超越了狮子
还拥有腐蚀能力极强的胃酸
不论是骨头还是腐肉都能消化
是几乎全能的清道夫
(叼着斑马尸骸的斑鬣狗,摄影师@李佳)
▼

秃鹫和秃鹳数量更多
它们在成堆的尸体上游弋
用巨喙清理着骨肉残渣
(站在尸体堆上的秃鹫,仿佛死亡的使者,在安抚逝去者的亡灵,图片来源@VCG)
▼

但也正是这些草原上的食腐者
抢在细菌之前完成了食物链的循环
避免了流行病的爆发与河流的污染
幸存下来的食草动物
也终于可以向着雨后的彩虹走去
它们抵达马赛马拉草原
在这里进入发情期
(马赛马拉草原上雄性斑马的求偶争斗,摄影师@贾纪谦)
▼

1个多月后
怀着新生命的种子
动物们踏上返乡的道路
它们会回到塞伦盖蒂
在重回绿色的草原上诞下后代
新生的小角马、小斑马呱呱坠地
用以分钟计数的时间学习着奔跑
只有如此才能活下来
并跟上几个月后迁徙的队伍
(新生的小角马,图片来源@VCG)
▼

与此同时
年幼的捕食者们也长大不少
再过1-2年
它们中的幸存者将学会独自捕猎
花豹和猎豹母亲也许会为自己的孩子
留下最后的一餐和自己的领地
(一只猎豹下树离开,摄影师@贾纪谦)
▼

成年的雄狮
也许会被赶出狮群
踏上流浪的旅程
建立自己的联盟
统治一片新的领土
(一只成年的雄狮,摄影师@李佳)
▼

年复一年
在这片草原上
生命的轮回无数次上演
即便是凶猛的捕食者
也只是因果链条中的一环
那么在这场被精确策划的“谋杀”背后
又隐藏着何种难以抗拒的力量?
02
草原
答案是一种普通的植物:草
草拥有极其广泛的适应性
它们遍布除南极以外的所有大陆
甚至被人类驯化成重要的粮食
在东非它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景观
热带稀树草原
(东非动物大迁徙所涉及到的主要热带稀树草原范围,制图@巩向杰&张靖/星球研究所)
▼

可以长到1米多高的草
在这里连绵无际
(热带稀树草原,图片来源@VCG)
▼

树木则零星分布
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
最多也只有30几棵
且树干歪歪扭扭
伞形的树冠枝叶稀疏
(热带稀树草原上的树木,摄影师@季凡)
▼

这是草的大陆,草的海洋
一个草的帝国
然而坐拥数量如此庞大的草
动物又为何要迁徙呢?
这源于草原随季节而发生的变化
对东非的草来说
水是最稀缺和重要的资源
在热带稀树草原上
每年都会有旱季和雨季的交替
而这将带来草原的兴衰枯荣
(东非草原雨季和旱季的交替,制图@王朝阳&张靖/星球研究所)
▼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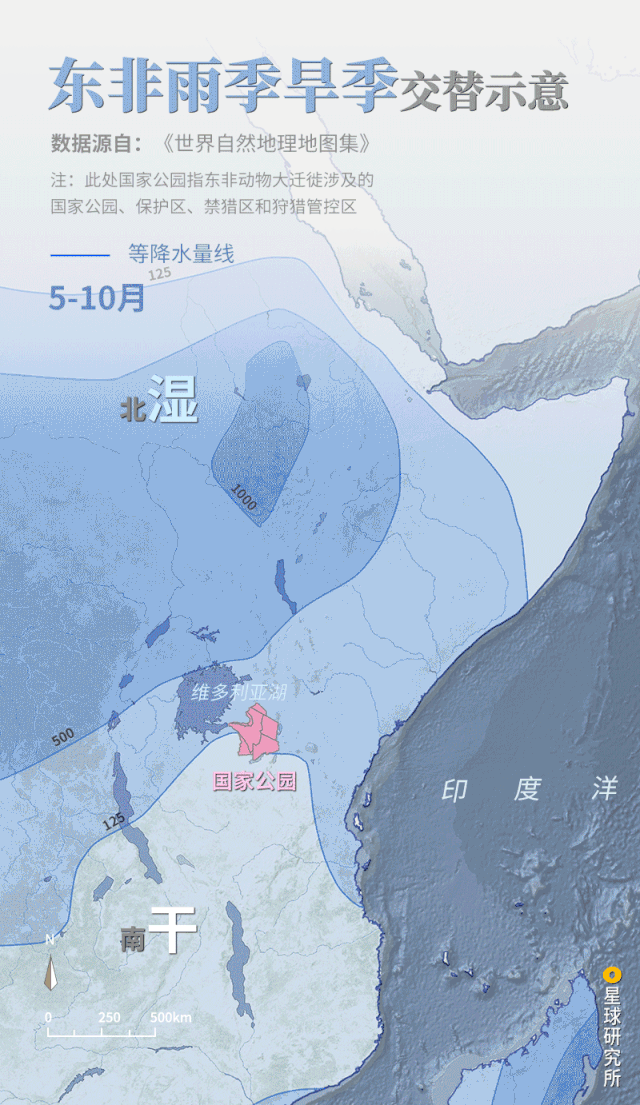
在旱季到来时
草原先是开始枯萎变色
呈现一派梦幻般的金黄
(8月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,旱季金黄色的草原上刮起了尘卷风,摄影师@程晓敏)
▼

然而随着雨水的进一步减少
金黄色的草原迅速衰败
成为一片近似荒漠的土地
日平均气温达到24-30℃
降水量却不足60㎜
河水断流,池塘干涸
留下风干的印记
(旱季草原上日渐干涸的河流,图片来源@VCG)
▼

过于干旱的草原
成了一个大燃料桶
一道闪电就能引发一场草原大火
火焰能将地表的干草烧光
(远处的草原大火,图片来源@VCG)
▼

然而当雨季来临
景象则完全不同
平均高达500-1000㎜的降雨量
让空气中的水分迅速增加
在阳光照射下时常形成彩虹
旱季被烧灼过后富含草木灰的土壤
此时成了新草生长最好的温床
阳光和雨水充沛,土壤养分充足
青草回归大地
(雨季返青的草原,摄影师@季凡)
▼

为了抓住短暂的雨季繁衍后代
青草迅速开花
一时间草原成了花海
充满杀戮的草原
此刻也格外宁静温情
(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里的草原花海与花海中的大象,摄影师@任国勇)
▼

表面上只是食物的草
实则是比动物更强大的“幕后力量”
它们通过自己岁岁枯荣的变化
就掌控了动物世界的战争与和平
并引发了食草动物的大迁徙
牵着它们团团转
但实际上
草原也被更强大的力量所控制着
03
裂谷
这就是东非高原
非洲最高的区域之一
这里的平均海拔超过1000米
高耸的地势改变了这里的大气环流
令高原之上形成了干-湿季交替的气候
此外从北方高纬度大陆而来的干冷信风
以及高原边缘山地对水汽的截留
更加剧了这里干燥的境况
东非高原上的水热条件
不再能支撑热带雨林的生长
(请横屏观看,恩戈罗恩戈罗自然保护区的高原地形,摄影师@贾纪谦)
▼

创造东非高原的力量
则隐藏在大陆地底深处
在地表之下约2900千米
是地幔与地核的边界地带
这里的一些物质上涌,直达地表
形成一个直径可达数千千米的“柱子”
是为超级地幔柱
从1300多万年前开始
地幔物质源源不断向上的涌动
将整个地表抬高
甚至在某些区域冲破束缚
(刚果金尼拉贡戈火山涌动的岩浆湖,摄影师@梦想家张先森)
▼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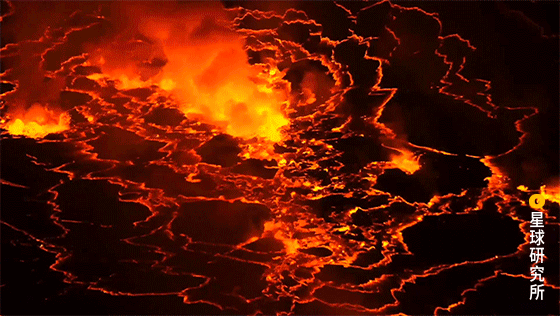
喷出地表的岩浆冷却后
层层堆叠为熔岩高原
进一步加高了东非的海拔
火山灰则覆盖了地表
形成富含养分的土壤
加剧了草的扩张
(尼拉贡戈火山活跃的火山口,摄影师@梦想家张先森)
▼

而已经沉寂的火山口周围
喷发物质堆出来的火山锥
就成了高原上最宏伟的风景
最著名的当属非洲第一峰
乞力马扎罗
5895米的高耸海拔
让这座位于赤道地区的火山
顶部仍有积雪甚至冰川
(乞力马扎罗山顶积雪,图片来源@VCG)
▼

由于山下的高原地势平坦
稀树草原上又没有树木的遮挡
乞力马扎罗山显得格外雄伟
(乞力马扎罗与山下的大象,摄影师@陈小琳)
▼

地幔物质对流的力量
将东非从中间拉开
最终形成一条巨大的裂谷带
东非大裂谷
它北起红海之滨
向南延伸至印度洋沿岸
贯穿整个东非
全长5500-6000千米
接近赤道周长的1/6
(东非大裂谷延伸及影响范围,制图@巩向杰&张靖/星球研究所)
▼

大裂谷的底部平坦开阔
边缘则被高耸的断层崖夹持
谷底与顶部的高差
可从数百米到两千多米
(东非大裂谷底部以及远处的裂谷边缘陡崖,图片来源@VCG)
▼

大裂谷底部是东非地势的最低点
来自周围山脉的地表流水
在重力作用下汇聚在谷底
形成了一连串湖泊
(裂谷带湖泊分布,制图@巩向杰&张靖/星球研究所)
▼

由于湖水大多汇聚在构造运动形成的裂缝中
因此这些构造湖形态狭长,湖底幽深
坦噶尼喀湖的深度就达到1435米
仅次于贝加尔湖
(太空中俯瞰坦噶尼喀湖,图片来源@NASA)
▼

又由于这里地势已经最低
因而裂谷底部的大多湖泊
缺少进一步外流的出水口
加上蒸发量巨大
这些湖泊成了盐湖
湖中含量极高的矿物质
供养了大量的细菌和藻类
也使湖泊呈现出鲜红的色调
(呈现红色的纳特龙湖,摄影师@蓦然白里小三黑)
▼

而以湖中微生物和小型动物为食的火烈鸟
也因食物中富含的类胡萝卜素
而获得了一身火红的羽毛
(火烈鸟,图片来源@VCG)
▼

裂谷之上
草原在生生死死
动物在兜兜转转
一些灵长类动物
学会了直立行走的新技能
他们的后代
正是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类
我们用解放出来的双手
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家园
(马赛人的家园,摄影师@梅元皎)
▼

而这整个精彩的世界
之所以被创造并延续下来
离不开裂谷之下的巨大力量
这种力量
源自一个动力不息的地球
纵观茫茫宇宙,万千星辰
只有地球
是目前我们已知的
唯一拥有如此丰富的景观
和如此多样生命形式的行星
(东非,伦盖火山脚下的湖泊和生灵,摄影师@梅元皎)
▼

每年5月的东非大草原上
大迁徙的序幕准时拉开
一场场残酷的杀戮如期上演
无数生命在这里生生死死,奔腾不息
年复一年遵循着
这颗星球上的“天地法则”
(奔走的斑马,图片来源@VCG)
▼

而相比这个宏大的世界
一只角马或一只狮子
它们的生命是如此微不足道
然而正是这些渺小的个体
却组成了一股巨大的生命洪流
让茫茫宇宙中这颗蓝色的星球
成为最独一无二的那一个
这就是生命
渺小
却又伟大的力量
(夕阳下的角马,摄影师@胡子捷森)
▼

파일 [ 3 ]



[필수입력] 닉네임
[필수입력] 인증코드 왼쪽 박스안에 표시된 수자를 정확히 입력하세요
왼쪽 박스안에 표시된 수자를 정확히 입력하세요